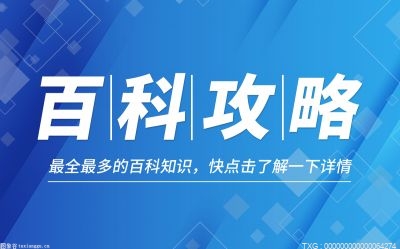■ 算法治理
 (资料图)
(资料图)
□ 杨丰帆
人工智能作为多种科学技术的融合体,既包括思维科学,也包括数据科学、统计科学等,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彰显出自身独有的价值与意义。但人工智能在应用的过程中,由于伦理规范不足等问题,出现了需要在刑事法律方面进行新调整的趋势。人工智能的介入提升了相关犯罪的技术性和危害性,使刑事风险出现新的特点,如何应对此种刑事风险特点,既是人工智能时代下刑法发展的重要探索,也是刑法维护公民主体权益的必要探索。
从本质上来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工具”,其行为受到人类主体的控制,人工智能所产生的法律意义与法律后果是需要归属到人类主体身上的。因此,应以“人”为切入点,构建人工智能刑事犯罪的主体,探究人工智能刑事犯罪的刑法应对路径。
在当前所处的“弱人工智能时代”下,人工智能及其产品不具有主动的刑事犯罪的意识和能力。然而,人工智能具有人脑的“仿生”性,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无法预测“强人工智能时代”中人工智能及其产品是否会突破人类主体的控制,亦或者说未来“仿生性”的强度可能会突破现有的认知。因此,在探究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过程中,既要立足于当下的现有科技和实践,同时也要从发展性的角度出发,防止陷入理论认识失范和立法认识失范的境地。
从当前研究现状来看,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主要是从工具应用风险进行考虑,智能科技的介入导致多类型刑事犯罪手段的升级。尤其体现在人工智能在互联网介质的作用下,与大数据等技术体系配合,在公民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领域对个人信息进行“打包”贩卖,形成新型的犯罪链条。这也是人工智能在人类主体控制下形成的新型刑事犯罪路径,进一步凸显人工智能所衍生出的新型刑事犯罪问题,本质上是人类主体借助新技术实施的犯罪行为,人工智能也自然成为此类犯罪的“工具”和中介系统。
从人工智能刑事风险来看,虽然人工智能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模式造成了改变,但却难以改变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的目的性、计划性等本质性内容。因而在对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特点进行解读时,应从刑法解释论出发,分析风险特点背后对刑法适用所造成的量的变化影响。
从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具体特点来看,主要包括犯罪行为方式的多元化、犯罪行为和犯罪对象的智能化两个方面。
首先,虽然人工智能尚未形成自身的独立人格,但是相对于其他技术而言,该技术又具备自主操作的能力,在部分方面也突破了人类行为能力的范畴,能够有效帮助犯罪行为人实现自身的犯罪目的,同时又能够采用多元的犯罪方式,降低犯罪的成本。例如,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结合,行为人能够通过算法植入和后台数据库入侵等多元形式,在几秒时间内获取海量的公民个人信息,以此进行牟利。同时,人工智能犯罪方式多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更多的犯罪行为和衍生案件,如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既遂的基础上,按照相关信息对公民进行诈骗、威胁、恐吓等,借助智能技术本身,对人的声音进行模仿和改变,进一步提升了刑事犯罪的隐蔽性,影响到后续公安机关对的案件侦破的速度与难度。
其次,人工智能以中介的方式介入到刑事犯罪中,也会出现犯罪行为和犯罪对象的智能化问题。行为人通过人工智能打破或者拓展传统犯罪的边界,使得犯罪的主动性和危害性进一步凸显。在司法实践中,淫秽色情录像传播案件,犯罪行为人结合传播对象的需求,借助人工智能进行“换脸”,构成对涉事人的侮辱和诽谤,而这种犯罪行为是对传统诽谤罪、侮辱罪边界的一种拓展,体现出智能型犯罪行为的特点。
在人工智能刑事犯罪责任主体的确定和量刑程度的判断方面,既要结合人工智能作为工具的使用情况,对行为人在案件中应当承担责任的大小进行判定,同时也要结合人工智能在案件中所起到的实质性犯罪价值和作用,进一步强化法律对人权的保护和惩罚。本质上,人工智能并非是超越人类的主体,而是借助人类科技赋能具备了一定的“仿生”能力,人工智能应用在刑事犯罪中,并未改变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更未改变刑法的实质性内涵。因此,在责任主体的限定上,仍要依据“人与人”的路径,以此来确保得到具有正当性的法律归责结果。
在刑事责任分配的过程中,要充分兼顾刑法公正的效果和威慑效果。人工智能刑事犯罪中所涉及到的主体,不仅包括实施具体犯罪行为的主体,同时也涉及到产品制造商等主体、被侵犯权益和权利的主体以及该群体背后所涉及到的其他社会主体,如何确保法律公平的实现和效果的最优化是该类刑事案件解决的关键所在。从本质上而言,在当前所处的“弱人工智能时代”下,人工智能产品不具有独立自由的意志,不能因人工智能出现于犯罪而对刑事责任分配的制度进行变革。人工智能产品被创造的目的在于服务人,而非是驾驭人或者成为独立自主的人,人工智能在刑事犯罪中的应用,主要是行为人自身意志的转移。因此,需要把握好刑事责任的唯一指向性,这也是法的意义和社会效果兼顾的前提。
最后,在应对人工智能刑事风险时要把握好刑事注意义务和监管义务。在理论界,有人认为研发者、生产者要对人工智能或产品应用过程中造成的社会危害、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此来将法律风险责任主体进行转移或者扩大。然而,从刑法所调整的范围和目的来看,义务层面虽然是责任构成的重要要素,但其具有“之一性”,而非“唯一性”,能够在刑事规则过程中作为基础依据之一,但是不能偏离刑事犯罪本身的行为人意志、具体行为的决定作用。所以,对于人工智能刑事犯罪中的刑事注意义务和监管义务可以结合具体情况作出参照和归责,却不能消解和转嫁刑事犯罪行为主体本身的责任。
在刑事犯罪中,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中介作用和人类的认识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鸿沟”,这导致了新型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出现,也造成传统犯罪行为边界的扩展,但是刑法调整对象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因此,在对人工智能刑事犯罪进行刑法规制的过程中,要结合具体案件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以及行为人主体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刑法本身的量变化探索和质变化演进,从而确保刑法在生活中的良性调整作用。